非告訴乃論自訴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讀享編輯團隊寫的 好看!四等總複習:2022司法特考 和康晞的 這題會考!民事訴訟法大意+刑事訴訟法大意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另外網站刑事訴訟法名詞解釋「告訴」 - 自訴」、「上訴」 之區別也說明:(二)在審判中撤回告訴,法院應依第303 條第3 款「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撤回後之效力: (一)撤回告訴之人,不得再行告訴,(§ ...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讀享數位 和學稔出版社所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研究所 謝煜偉所指導 凃冠宇的 展望未來的刑事責任概念-以修復式司法為契機 (2020),提出非告訴乃論自訴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責任、刑事責任、應答責任、展望未來的責任、修復式司法、批判性修復式司法、刑罰廢止論、告訴乃論。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高雄大學 法律學系碩士班 吳俊毅所指導 黃國恩的 論刑事審判程序之標的 (2018),提出因為有 訴訟標的、控訴原則、犯罪事實、案件單一性、案件同一性、追加起訴、公訴不可分、審判不可分、告訴不可分、一事不再理、罪數競合、刑事訴訟法第267條、刑事訴訟法第268條的重點而找出了 非告訴乃論自訴的解答。
最後網站常見問答-提起自訴有何限制? - 司法院則補充:但告訴乃論之罪,經犯罪之直接被害人提起自訴者,不在此限。 同一案件曾經被害人提起自訴後復撤回。 同一案件曾經被害人提起自訴後受駁回自訴之裁定確定,非有法定事由 ...
好看!四等總複習:2022司法特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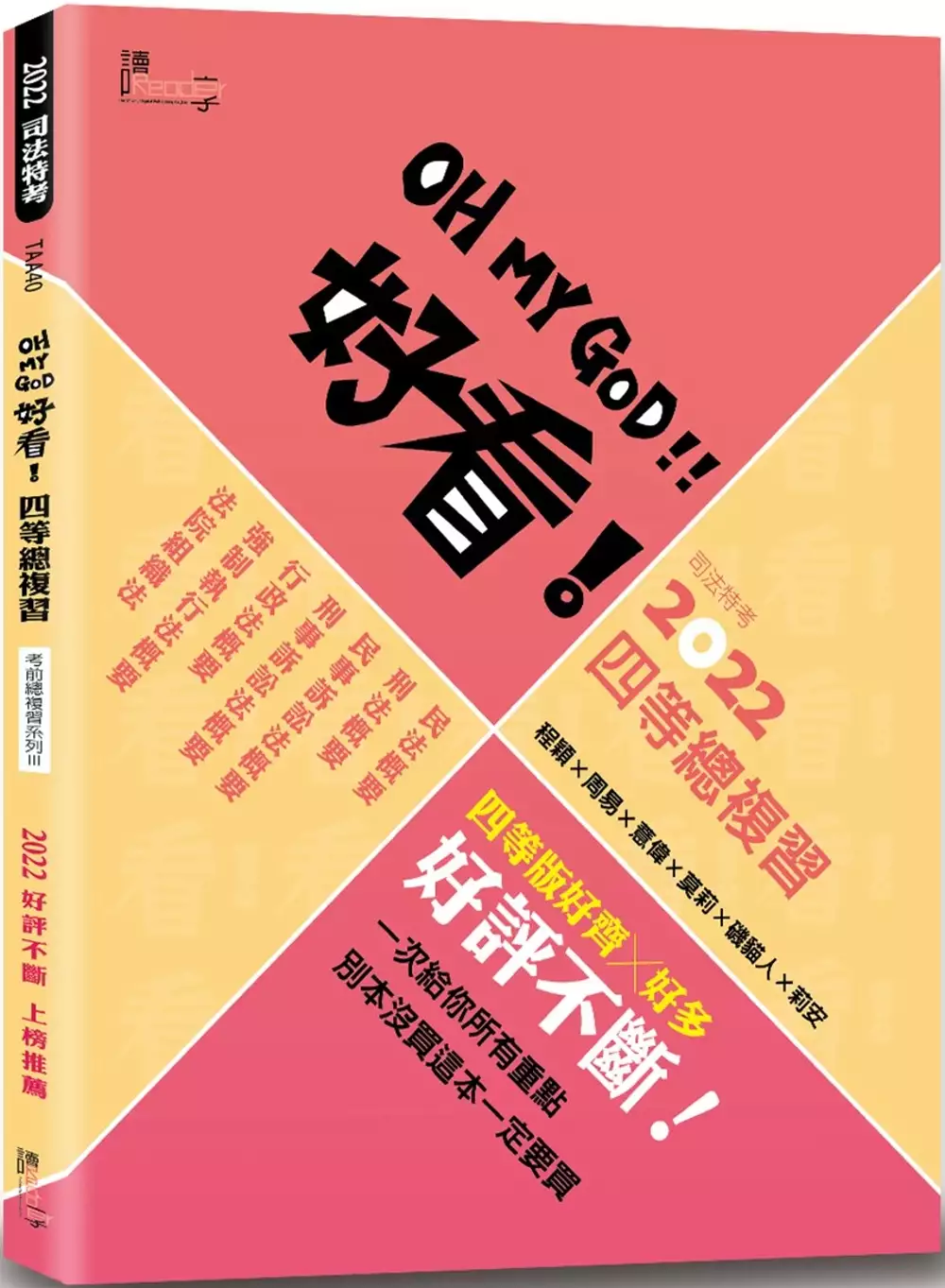
為了解決非告訴乃論自訴 的問題,作者讀享編輯團隊 這樣論述:
四等版好齊╳好多 好評不斷!一次給你所有重點 程穎╳周易╳薏偉╳莫莉╳磯貓人╳莉安 別本沒買這本一定要買
展望未來的刑事責任概念-以修復式司法為契機
為了解決非告訴乃論自訴 的問題,作者凃冠宇 這樣論述:
刑事司法系統是以責任制度作為其根基而運作,旨在對應犯罪事態,責任概念在犯罪論與量刑論具有的限定處罰機能,在刑事法領域內占據了重要的地位。然而隨著當代刑事政策的發展,責任概念變得更加空洞與稀薄,責任作為獨立的制度應有重新檢視的必要。現行刑事責任是以應報為基底採取負擔責任,係以責任的歸屬與清算為主,然而透過日本學者瀧川裕英所提出的應答責任論,本文認為刑事責任並非僅有回顧過去的應報責任,而是具有展望未來的一面,此種責任是直接開展於問責者與答責者之間,毋須透過國家高權介入進行責任的歸屬與分配,從責任實踐的觀點以及刑罰廢止論的觀點來看,應答責任是相較負擔責任值得採取的責任理論。應答責任論的具體實踐是修
復式司法,因此本文試著以應答責任論重新建構修復式司法的內涵,認為修復式司法應該要包含無目的、去國家化、對話、社群參與四個要素。以我國制度作為討論背景,本文也確認了我國修復式司法之面貌,並試圖以批判性修復式司法的分析指出傳統理論的未盡之處,具體的制度盤點包括了對於告訴乃論、緩起訴、量刑與緩刑制度的重新理解,希冀在現行制度內建立起起懸置或限制現行刑事司法的修復式司法場域。並且,透過以應答責任為基礎的修復式司法理論,本文認為修復式司法不應自我貶抑為刑事司法系統的補充性制度,而應該成為挑戰刑事司法、應報以及刑罰思想的批判性理論。
這題會考!民事訴訟法大意+刑事訴訟法大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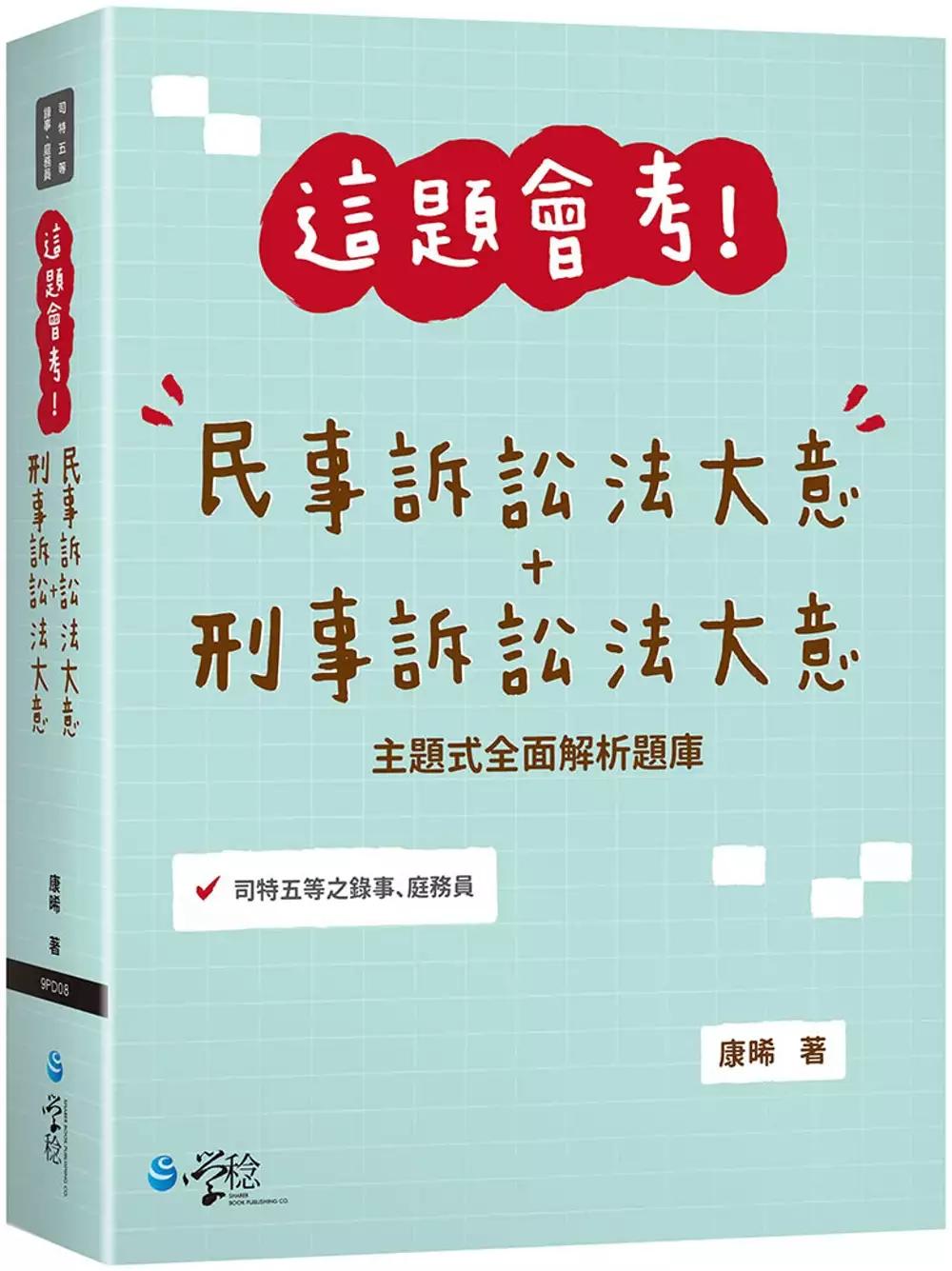
為了解決非告訴乃論自訴 的問題,作者康晞 這樣論述:
專供司特五等:錄事、庭務員 使用 ◆參酌考選部命題大綱編寫,呈現考試趨勢 ◆主題式重點整理,快速掌握學習關鍵 ◆統整表格清晰簡明,釐清各種概念 ◆雙色印刷,重點立現強化記憶 ◆主要收錄近10年試題及精選其他年度試題為補充,完整解析並用客觀大數據的方式標示星號,全面提升考試實力
論刑事審判程序之標的
為了解決非告訴乃論自訴 的問題,作者黃國恩 這樣論述:
訴訟標的,是訴訟法的核心內涵之一,「確定審判之範圍」、「判斷是否追加起訴」以及「確定判決的效力範圍」係由此出發。最高法院向來並未清楚說明刑事訴訟的訴訟標的為何,就聚焦在「案件單一性與同一性」之上,並且以「刑罰權單一且不可分」的理由,將「不可分」運用在各個程序階段。「不可分」是一個法律擬制的「效果」,要適用這樣的法律效果前,必須說明其背後的理由,將這樣的效果當成「理由」,恐有循環論證的疑慮。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67條公訴不可分的規定,實務向來是透過「實體法上一個刑罰權,訴訟法上一個訴訟客體」的基準來認定其適用範圍,換言之,犯罪事實在法院透過實體法罪數理論的判斷後,被認為是「一罪」時,訴訟
法上則為「一案件」,檢察官若僅起訴該犯罪事實的一部,則效力依然會及於檢察官未起訴的事實,法院仍須就事實的全部進行審理判決。反之,若法院認為檢察官未起訴的事實與已起訴的事實為「數罪」,則法院就不能依照「公訴不可分」的規定併予審理,必須由檢察官依照第265條追加起訴。 第267條所描述的情況是合理的,檢察官自己都無法保證,所起訴的就是犯罪事實的全貌,且基於訴訟經濟的考量,並無法堅持完全貫徹控訴原則所要求的不告不理,對被告甚至會有受到反覆起訴的疑慮。真正的問題在於「要如何認定犯罪事實的範圍」。實務上向來區分成案件「單一性」與「同一性」兩個問題層次來討論,但這樣的區別實益為何。無論是單一性或同一
性,所要討論的核心問題依然落在「如何認定犯罪事實的範圍」,因此,似乎沒有必要區分成兩種問題層次來討論,應當適用一套「共通」的基準來判斷此一問題。 實務採用實體法上「罪數」的標準來判斷訴訟法上「犯罪事實範圍」的基準,似乎並不合適,因為事實的全貌在「未經判決確定」之前,會不斷產生「浮動性」,如此一來,根據罪數理論得出的結論就會發生改變,被告的辯護範圍將無法確定。有學者提出德國法上的「自然的單一歷史進程」標準,來取代「罪數」,事實上,我國實務對於這種操作模式並不陌生,因為在同一性所適用的「訴之目的與侵害性行為同一」正是與「自然的單一歷史進程」相類似的內涵,只是描述上略有差異。本文將對以上問題與
實務運作的妥適性進行探討,並對此提出修法上的建議,以供參考。
非告訴乃論自訴的網路口碑排行榜
-
#1.非告訴乃論可以自訴嗎在PTT/Dcard完整相關資訊 - 媽媽最愛你
gl =TW › hl=zh-TW .非 ...法務部-法律問題新修正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一項: 同一案件經檢察官依第二百二十八條規定開始偵查者,不得再行自訴。 但告訴乃論之罪, ... 於 babygoretro.com -
#2.法律時事評論-什麼是「訴」?非告訴乃論 - 法操
【刑法小教室】什麼是「訴」?非告訴乃論、告訴乃論與自訴 · 如果是「絕對告訴乃論之罪」,就必須有人提告,檢察官才能合法起訴。 · 「相對告訴乃論之罪」指的是,本來屬於「 ... 於 follaw.tw -
#3.刑事訴訟法名詞解釋「告訴」 - 自訴」、「上訴」 之區別
(二)在審判中撤回告訴,法院應依第303 條第3 款「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撤回後之效力: (一)撤回告訴之人,不得再行告訴,(§ ... 於 plus.public.com.tw -
#4.常見問答-提起自訴有何限制? - 司法院
但告訴乃論之罪,經犯罪之直接被害人提起自訴者,不在此限。 同一案件曾經被害人提起自訴後復撤回。 同一案件曾經被害人提起自訴後受駁回自訴之裁定確定,非有法定事由 ... 於 www.judicial.gov.tw -
#5.非告訴乃論可以自訴嗎 - 你不知道的歷史故事
新修正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一項: 同一案件經檢察官依第二百二十八條規定開始偵查者,不得再行自訴。 但告訴乃論之罪,經犯罪之直接被害人提起自訴者,不在此限。 於 historyslice.com -
#6.何種情況下不能撤告看懂告訴乃論跟公訴罪差在哪? - YouTube
本集重點:一、《刑法》中 告訴乃論 和 非告訴乃論 的定義與區別二、何謂告訴不可分原則?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訂閱與分享加上小鈴鐺給他開起來! 於 www.youtube.com -
#7.傷害罪構成要件是什麼?成立傷害罪,必須先符合這點!
不論被告後來是否有屢行和解條件,都不可以再提起自訴或是公訴。 (三)重傷罪非告訴乃論. 當今天所受到的傷害已經造成「身體某個器官」嚴重受損 ... 於 laws010.com -
#8.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 法務部-法律問題
新修正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一項: 同一案件經檢察官依第二百二十八條規定開始偵查者,不得再行自訴。但告訴乃論之罪,經犯罪之直接被害人提起自訴者,不在此限。 於 mojlaw.moj.gov.tw -
#9.提出刑事告訴之條件為何?撤回告訴之效果如何?
但告訴乃論之罪,不得與被害人明示之意思相反(刑事訴訟法第233條第2項)。 (四)刑法第230條之妨害風化罪,非左列之人不得告訴(刑事訴訟法第234條第1項) ... 於 www.vac.gov.tw -
#10.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
駁回自訴之裁定已確定者,非有第二百六十條各款情形之一,不得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自訴 。 第三百二十七條 ... 自訴論。其非告訴或非請求乃論之罪,不待其陳述而為判決。 於 www.laws.taipei.gov.tw -
#11.請問告訴乃論,自訴與公訴的問題- 法律
由檢察官追訴犯罪,其中包含非告訴乃論(這代表國家公益立場,較無問題) : 2.經由被害人提起告訴,經檢察官認為有犯罪嫌疑時,進行追訴犯罪的告訴乃論 於 legal.faqs.tw -
#12.[問題] 請問告訴乃論,自訴與公訴的問題- 看板LAW
就小弟"有可能錯誤"的認知公訴--1.由檢察官追訴犯罪,其中包含非告訴乃論(這代表國家公益立場,較無問題) 2.經由被害人提起告訴,經檢察官認為有犯罪嫌疑 ... 於 www.ptt.cc -
#13.楊貴智|什麼!?所有犯罪其實都可以提起公訴罪? - 法律 ...
相反地,我國也允許被害者自行搜集證據、追訴犯罪,此時刑事訴訟並不是由檢察官代表國家提起,而是被害人自行提起,因此稱為自訴。 那什麼是「告訴乃論之 ... 於 plainlaw.me -
#14.刑事訴訟程序簡介- 關於協會- 新聞訊息
當人們觸犯刑事法律,法院便會因公訴、自訴的提起,依循一定的程序、適用法律,予以判決結果。 ... 屬於告訴乃論之罪的整理,可以參見此網站。 於 www.cda.com.tw -
#15.「非告訴乃論」之罪,即俗稱之公訴罪。(刑事) @ DataBase
Source:眾律國際法律事務所一、「告訴乃論」之罪與「非告訴乃論」之罪指需經告訴 ... 公訴乃透過檢察官而提起之刑事訴訟;而自訴即自訴權人(被害人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 ... 於 blog.xuite.net -
#16.妨害自由是公訴罪嗎 - 07Nan
妨害自由罪章多數為非告訴乃論,也就是俗稱公訴罪,妨害自由公訴一旦提告便無法撤告! 檢察官會依職權進行調查,並做出是否起訴的處分,決定是否讓案件進到一審法院進行 ... 於 www.07nanyan.co -
#17.刑事訴訟法-自訴(二)-知識百科-三民輔考
自訴 之撤回提起自訴之人就告訴乃論之罪,得撤回自訴。擔當自訴之檢察官,因非當事人,故無撤回權。 於 www.3people.com.tw -
#18.搜尋:告訴乃論之罪與非告訴乃論 - 阿摩線上測驗
自訴 提起告訴乃論之罪,自訴人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可以撤回自訴;但是非告訴乃論之罪,為避免自訴人利用自訴程序以洩忿或恫嚇被告,不准撤回自訴。其撤回不發生效力,法院仍 ... 於 yamol.tw -
#19.「公訴」與「自訴」、「告訴乃論」之罪與「非告訴 ... - Orz 網摘
由於我國刑法將若干犯罪規定為,需經告訴乃得論究,即需有告訴權人依法提出告訴[1],國家方得對犯罪行為人之犯行加以追究、處罰,因此實務上通稱此類犯罪 ... 於 orzhd.com -
#20.什麼是告訴乃論與非告訴乃論?和公訴與自訴有什麼... - 伴侶
前往什麼是告訴乃論與非告訴乃論?和公訴與自訴有什麼... - 法律百科. 2022-03-17. 文章推薦指數: 80 %. 投票人數:10人. 您即將離開本站,並前往什麼是告訴乃論與非 ... 於 hkskylove.com -
#21.告訴乃論之罪和非告訴乃論之罪 - 天秤座法律網
檢警若是知悉而不偵辦,則會夠成刑法第127條的瀆職罪。簡單說,「非告訴乃論之罪」被害人不論是否告訴,只要檢察官知道有犯罪嫌疑,即得偵查起訴,例如 ... 於 www.justlaw.com.tw -
#22.第二章自訴
會使得全部均不得提起自訴。 單一案件,犯罪事實之一部為告訴乃論之罪,他部為非告訴乃論之. 罪, ... 於 publish.get.com.tw -
#23.司法小辭典:公訴/自訴- 非告訴乃論罪 - 月旦知識庫
司法改革雜誌編輯部,現行刑法中屬告訴乃論的強姦罪是否應採公訴罪?此議題目前仍在立法院討論中,但根據日前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七成五的民眾都,月旦知識庫, ... 於 lawdata.com.tw -
#24.性侵害犯罪告訴乃論與非告訴乃論一覽表
非告訴. 乃論. 1.原為告訴乃論,自九十年. 元月一日起改為非告訴乃. 論。(刑法施行法第九條之. 二). 2.對配偶犯強制性交罪. 者,仍為告訴乃 ... 於 www.fhsh.tp.edu.tw -
#25.高中社會科- L7: 告訴乃論與非告訴乃論
自訴 :是指犯罪之被害人或其特定親屬,在刑事案件中,不經偵查程序,由被害人或特定親屬逕向該管法院請求追訴。 另所謂「非告訴乃論之罪」被害人不論是否 ... 於 hs.nnkieh.tn.edu.tw -
#26.詐欺告訴乃論還是非告訴乃論?公訴自訴都能和解撤告嗎?
詐欺罪一般屬於非告訴乃論之罪,檢警機關一旦知悉就須依職權調查偵辦,不能藉由和解撤告,只有在詐欺的對象和詐欺行為人之間具有一定的親屬關係時,案件才會轉為告訴乃 ... 於 www.howlawyer.com.tw -
#27.第八章自訴制度比較
澳門刑訴法和刑法中都有“非經告訴不得進行刑事程序”和“非經自訴不得進行刑事程序”的規定,前者即 ... (二)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已不得爲告訴或請求者,不得再行自訴。 於 www.macaudata.com -
#28.告訴乃論與非告訴乃論- 法律知識庫聯晟法律
自訴 :是指犯罪之被害人或其特定親屬,在刑事案件中,不經偵查程序,由被害人或特定親屬逕向該管法院請求追訴。 另所謂「非告訴乃論之罪」被害人不論是否 ... 於 www.rclaw.com.tw -
#29.熊秋红:论公诉与自诉的关系 -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
二是一般人告诉,是指非被害人或其亲属的第三人,得知犯罪事实和犯罪人后,向官府 ... 北洋政府时期的《刑事诉讼条例》中所规定的自诉范围仅以告诉乃论之罪中的七种 ... 於 www.procedurallaw.cn -
#30.自訴與公訴 - 玉鼎法律事務所
但告訴乃論之罪,經犯罪之直接被害人提起自訴者,不在此限。 於開始偵查後,檢察官知有自訴在先或前項但書之情形者,應即停止偵查,將案件移送法院。 於 www.we-defend.com.tw -
#31.妨害名譽告訴乃論– 告訴乃論之罪有哪些 - Tsukaiend
什麼是告訴乃論與非告訴乃論?和公訴與自訴有什麼不同?|法律百科Legispedia. 【新聞疑義107】具狀撤回妨害名譽告訴,被告將不起訴? 【刑法第309條、310條】遊戲平台 ... 於 www.tsukaiend.co -
#32.非告訴乃論之罪不是公訴 - 法.師.說.法
「非告訴乃論之罪」與「公訴罪」不盡相同。非告訴乃論之罪,係檢察官於偵查時認為有犯罪嫌疑時,乃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依法對於犯罪嫌疑之人予以起訴 ... 於 saylaw2014.pixnet.net -
#33.何謂非告訴乃論 - 蘇狀師談法律
我國刑法或特別刑法或其他法律有刑事責任規定者,並沒有公訴罪這個名詞。 我國刑事訴訟法有公訴程序以及自訴程序,要弄清楚這是程序法講的是訴訟要進行 ... 於 j83804161.pixnet.net -
#34.院總第246 號 - 立法院
一、本法第三百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得提起自訴之犯罪之被害人,本不以刑法之特定罪章或罪名 ... 自訴。但告訴乃論之罪,經犯罪之直接被. 害人提起自訴者,不在此限。 於 lci.ly.gov.tw -
#35.刑事訴訟法告訴制度之重要爭點(下) - 公職王
至非告訴乃論之罪,縱係數人共犯一罪,要不過為一種相牽連案件,並不適用告訴不可分之原則,自得對於共犯中之一人單獨起訴。本件被告某甲與某氏結婚係同犯一個重婚罪,自訴 ... 於 www.public.tw -
#36.109 司律【刑法刑】 座
高法院二十四年上字第四九七四判例『犯人自行,在刑法上既非之行為, ... 輕罪之告訴乃論之罪分仍不得提起自訴始符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三條第. 一之立法意旨。 於 law.knu.edu.tw -
#37.「非告訴乃論」之罪,即俗稱之公訴罪。(刑事) - Uystm
「公訴」與「自訴」,「告訴乃論」之罪與「非告訴乃論」之罪– … 而因有告訴乃論之罪,相對地,實務上就將其他非此類之犯罪稱為「非告訴乃論」之罪,即俗稱之公訴罪。 於 www.optics4you3.co -
#38.刑事告訴與自訴有何不同? - 泓廷商務法律事務所
刑事案件又分二種,一種是「告訴乃論」的案子;另外一種是「非告訴乃論」的案子。「告訴乃論」就是要被害人有意思有追究時才會查辦,例如:毁謗、 ... 於 omniservice.com.tw -
#39.怎麼提告? - 法律扶助基金會
但告訴乃論之罪,經犯罪之「. 直接被害人提起自訴者,不在此限。 撤回自訴之人,不得再行自訴。 我上次撤回. 這次還想告. 於 www.laf.org.tw -
#40.20151002104125_題目卷 - 新北市立光榮國民中學
(A)一般行政訴訟(B)民事糾紛(C)告訴乃論的刑事案件(D)非告訴乃論的刑事案件。 ... (A)自訴、公訴(B)公訴、自訴(C)告訴、他訴(D)告訴、自訴。 於 www.grjh.ntpc.edu.tw -
#41.什麼是告訴乃論與非告訴乃論?和公訴與自訴有什麼不同?
例如刑法第287條規定刑法第277條的普通傷害罪須告訴乃論,因此被打到受傷的人若沒有提出告訴,檢察官即使知道這件事也無法起訴打人的人。則既然欠缺檢察官起訴,法院自然 ... 於 www.legis-pedia.com -
#42.事故所引發的法律問題-刑事責任
車禍引發刑事責任的追訴可分為公訴、自訴二類如下: ... 非告訴乃論:如過失致死罪不待告訴,法院即得追訴,警察機關現場處理完畢,即將案件移送檢方偵辦。 於 td.police.gov.taipei -
#43.意外事故刑事訴訟 - 碩豐法律事務所
又告訴應向有偵查權之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為之,被害人對於告訴乃論之罪未 ... 相對於上開公訴程序,由自訴人(被害人或遺屬)主動向法院提起刑事訴訟 ... 於 shuofeng.com.tw -
#44.告訴乃論仍為公訴 - 阿空的法律學習筆記
以上這些,在某些「非告訴乃論之罪」也是一樣--例如強制性交案件的被害人 ... 自訴. 「自訴」才是與「公訴」相對應的概念。是由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 ... 於 law-learning-note.blogspot.com -
#45.告訴、告發、公訴、自訴 - 馬克林的世界- 痞客邦
刑事案件又分二種,一種是「告訴乃論」的案子;另外一種是「非告訴乃論」的案子。「告訴乃論」就是要被害人有意思有追究時才會查辦,例如:毁謗、侮辱、非商業性的 ... 於 markyslin.pixnet.net -
#46.非告訴乃論,公訴、自訴之區別/ 學習律師蘇思鴻
而非告訴乃論恰與其相反,若檢察官主動偵查認定有犯嫌,即可提起公訴,無需被害人提出告訴。至於所謂的自訴,任何犯罪只要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要件,都 ... 於 zoomlaw.pixnet.net -
#47.女子取快递被造谣自诉转公诉案等入选最高检指导性案例
对公安机关未立案侦查,被害人已提出自诉的,检察机关应当处理好由自诉向公诉程序的转换。 ... 侮辱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於 j.021east.com -
#48.對刑事法關於告訴、公訴及自訴概念的解釋 - Facebook
告訴乃論 和非告訴乃論所要講的是,國家追究犯人刑事責任的時候,要不要以被害人或某其他特定人的告訴為要件。 2️⃣對於告訴乃論的犯罪,例如毀損罪或公然侮辱罪 ... 於 zh-cn.facebook.com -
#49.自訴-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公訴與自訴是訴訟主體的不同(檢方提出公訴,被害人提出自訴),告訴乃論與非告訴乃論是訴訟程序的不同,公訴不等於非告訴乃論,自訴不等於告訴乃論;所以「公訴罪」 ... 於 zh.wikipedia.org -
#50.【法律學堂】事實上法律沒有公訴罪 - 律師真心話
非告訴乃論 之罪就是,犯罪不必經過被害人或其他有告訴權人提出告訴,檢警就應該 ... 自訴:由被害人自己提起,但因為因為被害人可能不具有像檢察官一樣的法律能力, ... 於 chehan0310.pixnet.net -
#51.告訴乃論
刑事訴訟存在「公訴」與「自訴」兩種模式,前者是由檢察官代表國家起訴被告,後者則是由被害人自行對被告提起訴訟。告訴乃論與非告訴乃論只是起訴條件的差異,所適用的 ... 於 www.wikiwand.com -
#52.非告訴乃論之罪,有沒有「無罪和解」的機會? - 關鍵評論網
一般而言,犯了非告訴乃論之罪,縱然事後取得被害人完全原諒,被告若能得到個緩刑判決就已算很不錯,要完全脫罪十分困難,但是否有可能透過默契操作, ... 於 www.thenewslens.com -
#53.詐欺罪和解就不用判刑了嗎? - 颺理法律事務所
一、詐欺罪是非告訴乃論之罪,也就是俗稱“公訴罪”,非告訴乃論之罪就算被告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檢察官還是有可能將被告起訴的。 二、檢察官會勸被害人與被告和解,通常 ... 於 www.youngli.tw -
#54.刑事訴訟法理論與運用 - 第 526 頁 - Google 圖書結果
甲另外,自訴案件區別告訴乃論與非告訴乃論之罪,其實益在: 1.依§325I,告訴乃論之罪,自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自訴,而非告訴乃論之罪則否。 2.告訴乃論之罪, ... 於 books.google.com.tw -
#55.告訴乃論與非告訴乃論 - 一起讀判決
至於所謂公訴或自訴所要講的,是由誰來向法院請求審判的意思。檢察官和法官雖然都是從事法律工作的人,不過性質是不一樣的。檢察官是代表被害人的意思,也 ... 於 casebf.com -
#56.中信聯合法律事務所
自訴 提起後,如果是告訴乃論的罪,例如普通傷害罪,自訴人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前是可以撤回自訴;惟非告訴乃論之罪,是不可撤回自訴的。例如自訴被告詐欺後,自訴人與被告 ... 於 www.jangshin-law.com.tw -
#57.我要回覆] 討論主題 關於開始偵查後得否自訴問題 發表人 疑問 ...
同一案件於檢察官偵查後,自訴人就告訴乃論之罪,固仍得提起自訴,但該告訴 ... 亦即裁判上一罪之重罪(非告訴乃論)部分,若先經檢察官開始偵查,其 ... 於 www.lawspace.com.tw -
#58.彌補正義缺口的自訴制度 - 全國律師聯合會
但告訴乃論之罪,經犯罪之直接. 被害人提起自訴者,不在此限。」)。不過在. 非告訴乃論之罪的案件中,一旦被害人以告訴. 人身份聲請證據保全,依照現行法公訴優先 ... 於 www.twba.org.tw -
#59.20、自訴的要件為何? - 謝心味律師法律服務網
同一案件經檢察官依第二百二十八條規定開始偵查者,不得再行自訴。但告訴乃論之罪,經犯罪之直接被害人提起自訴者,不在此限(刑訴323條) 。 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者,非經 ... 於 www.swlaw.com.tw -
#60.自訴不是訴訟基本權; 自訴制度合憲嗎? - 在野法潮
至於自訴制度與憲法是否毫無扞格,則非無疑。 至少曾有兩則憲法解釋涉及自訴制度的憲法評價。釋字507 號解釋原是在處理告訴權的問題,但解釋文中卻將自訴權的法律限制 ... 於 bwc.businessweekly.com.tw -
#61.【刑訴】「告訴」與「自訴」之關係- 吾法吾天- udn城市
【試題】被害人先行告訴後,可否對同一案件再提起自訴?試說明之。 【擬答】. (一)不論告訴或非告訴乃論之罪,告訴均為開始偵查之原因,在告訴乃論 ... 於 city.udn.com -
#62.刑事自訴
如何提起刑事案件之自訴─兼論自訴與告訴乃論如何操作. 或許大家都有跟互助會之愉快或慘痛的經驗,而說到要如何告倒會的人《詐欺》,常常有人將『告訴和非告訴乃論之 ... 於 www.liha.com.tw -
#63.非告訴乃論自訴
於告訴權人有提出告訴,但嗣後撤回(法律並未限制告訴人於此類犯罪不得撤回告訴)之情形,亦同。. 二、「公訴」與「自訴」. 而一般將非告訴乃論之罪稱為公訴罪,其實 ... 於 bichler-shop.ch -
#64.請問非告訴乃論可以自訴嗎? - Clearnote
可以阿,只是非告訴乃論是指只要檢查官知道了,就必須主動偵查,就算之後想要和解也無法. ... 那被害人自訴了檢查官還要查嗎? 於 www.clearnotebooks.com -
#65.110年民事訴訟法大意與刑事訴訟法大意 - 第 556 頁 - Google 圖書結果
關於自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對於直系卑親屬,不得提起自訴(B)撤回自訴之人,不得再行自訴,但得提出告訴(C)告訴乃論之罪,雖逾告訴期間而不得告訴,但得再行自訴(D) ... 於 books.google.com.tw -
#66.【律師專欄】「告訴」與「自訴」有什麼不同 - 鈞誠法律事務所
非告訴乃論 :即使被害人不想追究,檢察官如果知道,也應該主動偵辦,例如:詐欺、背信的案件。 註:有些案件如性侵害的案件,以前是屬於「告訴乃論」,近 ... 於 www.jclaw.com.tw -
#67.刑事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被害人還可以提起自訴嗎?
若同一案件,檢察官已著手偵辦開啟偵查程序,案件已進地檢署,則被害人不得再向法院提出自訴。 但有一個例外,告訴乃論之犯罪(例如妨害名譽、傷害、毀損 ... 於 www.lawyerli.tw -
#68.執法者應本於良心行政讓人民免於恐懼 - 奇摩新聞
... 都刻錯,還有自訴人到庭稱沒有要提自訴,或出庭後所陳竟與自訴狀內容不符,甚至還發生自訴人對所提非告訴乃論之詐欺罪,於訴訟中具狀撤回自訴。 於 tw.stock.yahoo.com -
#69.非告訴乃論即為公訴罪(C) - 題庫堂
易言之,公訴乃透過檢察官而提起之刑事訴訟;而自訴即自訴權人(被害人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直系血親或配偶)自己提起的刑事訴訟。此外,我國法律並未規定告訴或非告訴乃 ... 於 www.tikutang.com -
#70.【律師專欄】刑事告(自)訴指南
由於自訴人非檢察官,法律特別規定,法院對於自訴案件,於調查證據發現非屬刑事案時,可勸自訴人撤回。又,自訴人對「告訴乃論」罪提起自訴時,也可在審判程序結束前 ... 於 law.moeasmea.gov.tw -
#71.刑事訴訟法第327、329、331
告訴 或請求乃論之罪,自訴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或到庭不為陳述者,以撤回自訴論。其非告訴或非請求乃論之罪,得不待其陳述而為判決。 於 www.lawbank.com.tw -
#72.如何自訴才合法? 作者: 蘇南桓 - 永然文化出版
另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須告訴乃論,而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人知悉犯人之時 ... 之時起已逾六個月法定告訴期間,始對被告李四瑞傷害部分追加提起自訴,自非合法。 於 book.law119.com.tw -
#73.刑事訴訟法(下): 律師.司法官.法研所 - 第 8-36 頁 - Google 圖書結果
葉康駕駛免費台灣跡J易宣傳車,不慎同時撞上乙(過失傷害為告訴乃論),且撞死丙(過失致死為非告訴乃論),二者為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丙的家屬先告訴後,乙可否自訴? 1. 於 books.google.com.tw -
#74.焦點判決| 元照出版
關鍵詞:自訴,非法人團體,外國公司,法人,被害人. ... 自訴,同時國家針對自訴程序得予追訴之犯罪,仍有訴追權益(若是請求或告訴乃論之罪,則須視是否 ... 於 www.angle.com.tw